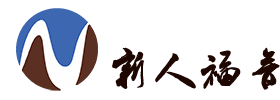天凉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世记三章八至九节)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年代。仍依稀记得,半夜里母亲将我从熟睡中抱起,去参加游行。一九七六年以后,在“科学救国” 的口号下,全国上下都迎接“科学的春天”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潮流里,上大学成了我的梦想。
八十年代初,我终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世人羡慕的佼佼者!想到毕业后将成为身穿白大褂,出入病人中,救死扶伤的医生,自觉高尚无比。数年寒窗之后,如愿被分配到一家大医院,担任眼科医生。二十岁出头的我,立下一生之愿:“这一生不做金钱奴隶,不求政治光环,只要做一个真正能使人重见光明的全国一流的眼科大夫。”
接下来的几年,自然不轻松。我穿梭于门诊、病房、科室,找名医拜师、到好医院进修,搞课题、做研究、出文章、写新书。白天忙病人,晚上写稿子。几年下来,由一个生疏的实习生,到能独当一面,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收红包的人。正当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朝着目标越来越近时,有两个奇怪的感觉在我里面越来越强烈。一个就是把自己“出卖了”的感觉。因为,为着搞好关系,对主任总要阿臾奉迎,溜须拍马;对同事明中左右逢源,暗中争竞忌妒。原本想过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但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承认一个事实,我已经跳进了一个大染缸─不管我情愿还是不情愿。如果大学刚毕业,我还是一件“白衬衫”的话,几年以后的我,已经“灰不溜秋”。而且心里很清楚,越想往上,就越不能顾是白是黑。虽然朋友说我“混”得真不错,但我只能苦笑,甚至觉得再继续下去,可能会把自己的人格都给卖光了。
另一个就是“不怎么样”的感觉。虽然表面看似春风得意,但心里却想,“也不怎么样啊! 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做一个‘好医生’而已吗?” 一面好象快达到目标,一面又失去了目标…
正值我和丈夫的事业处于黄金阶段时,我俩突然想要出国─能自由发展,可能可以闯出一条“金光大道”来。一九九三年,因我先生有机会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于是我们来到了美国。
来美后第一周,我俩到朋友家聚聚。一上公车,拿了一张二十元美金向司机买票,司机说“No”,原来这是个无人售票车。二十元全丢下去太傻,下车换钱又怕迟到。这时有人主动来换零钱,让我们觉得美国真不错。另有一位身穿黑衣的女性,看我们象是刚来的,就主动问候。临下车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教会,并且向我们要电话号码。平常非常谨慎的丈夫,不知怎么搞的,还真的拿笔写下了号码。
虽然号码给出去了,但我俩根本没有一点当真。要来的周末,两个人在家里,真是无聊透顶。这时电话铃响了,来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我先生说,“反正没事,既然来到美国,就去看看‘外国的神’长什么样子。”
一进屋子,看到好多中国人,就颇感温暖。后来聚会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但是对几个讲话的人面光发亮很有印象。虽然那个聚会气氛不错,但当我出门时,一阵子凉风吹来,我晃晃脑袋,开始责备自己:“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我来美国是要干一番事业的,不是跟这一班莫名其妙的人混的”。于是将这件事全都抛到脑后。过几天有两个来自教会的人来访,拚命劝我们信神。我俩想,我们好好的,要神干什么,硬是客客气气地把人打发走了。
当时我在餐馆打工。事后我对餐馆老板说,“昨天晚上有两个人来我家,硬要我信耶稣,搞到快十一点还不走,真是讨厌!”老板看看我,说,“你说什么?我就是基督徒!”我听了一楞,心想这下倒霉了,不想听“那些”大概都不行了。老板虽然不会强迫我,但偶尔也会讲一点,说神如何听她祷告啊,让她总是很喜乐很平安。还劝我遇到事情,也可以试着祷告。表面上我没说什么,心里却想,你是一个做老板的有钱人,吃饱饭无聊没事干,找一个主耶稣信信,解解闷也不错。但我是个靠一双手闯天下的人,哪里有这么多闲功夫。所以老板再讲,我也只是随便听听而已。
过了一、两个月,餐馆两个厨师同时辞工不干,搞得老板措手不及,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人。我来美国没多久,认识人不多,万般无奈下,打电话给了教会的人。说来真巧,来了一位厨师,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个大陆人。
这一下可热闹了。跟老板我不敢顶嘴,跟他说话我就直截了当了。问他,“你给我‘老实交待’,你信主是真是假,如果跟我说是假的,我绝不会笑话你,只要说老实话。”他说,“真的”。我紧迫盯人,问,“那是为着什么目的,不是物质的,大概也是为着精神的吧?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脑子不胡涂。”他拼命跟我解释,有时差一点吵起来。他说有神,有证据可以证明有神,我就说,“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看啊,否则没神。” 有一次他急了,对我说,“我说不过你,反正有神!”就不再说话了。我心里暗暗得意:证据不足,认输了吧!但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升起来:“你真的那么有把握,说没有神?”我诚实地对自己说,确实没有把握,但心里又想:就算真正有神,与我何干,没本事的人才去信神,我不用信。
在餐馆我是一个收银员,空闲下来,就要帮着做事。常常需要切两箱鸡块,一箱二十磅。有一天我切着切着,回想起以前上班的情景,就放下刀,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原本应是拿着眼科手术刀啊,如今我的前途在哪里?美国虽是自由,但这就是我的美国梦吗?
我老板因为家庭背景特殊―父亲颇有身份地位,所以她常和上流社会的人来往:有的是卓越的科学家,有的是成功的生意人,也有一些是有名望的文人,其中有一个居然还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她常常带我出入于这些看似很有成就的上流人士中间。但多次接触以后,里面却产生了非常强的失落感。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没什么意思:今天请吃饭,明天去喝咖啡,要么去听音乐或者去游泳,去健身房,或是以什么别的花样来打发时间。我想,在工作上我最多只能达到他们这样的成就。若真达到了,大概也是过这样的一个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我只觉得虚空无聊透顶。看着他们,就好象看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我,就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位,我似乎看到了人生的终局! 这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难道人的一生,最好也不过就是这样吗?但若不是这样,我又想怎样呢?同样的彷徨,再一次更强烈在我心中兴起。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面因为环境的变迁,心里很苦;一面又因无聊而深觉虚空,这种又苦又空的感觉,压在我里面。终于有一天,我向老板辞工。我觉得需要好好考虑人生的前途,要作一个最合理、最智慧的打算。我想重操旧业当医生,但一笔相当大的投资从哪里来?若找一个最有前途的专业,再进校门从头来,那丢掉干了多年的老本行,不是太可惜了?无论走哪一条路,我知道这一脚踩下去,是没有回头路的。正在举棋不定时,心想不如多问问人,或许会遇到高人指点。未料,问的结果是众说纷纭,使我难以定夺。
有一天想到,信主的人说不定有什么好主意,就打电话请教。那个弟兄当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又跟我谈“无聊”的。我觉得既然是我有求于他,自然要让他三分。等他讲完轮到我时,才将为难我的问题提出来,问他有何高见。他说, 你问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个意见,不如问问神,其实祂早就知道了。我心里想,这么大的事,交给一个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去办,万一搞砸了怎么办?但我不便明说,便搪塞地说,这怎么问哪?他立刻说,“祷告啊!” 我心想,不必了。
但又觉得实在不礼貌,就脱口而出说,“我不会啊!”这位弟兄说,“不会不要紧,我带你祷告就行了。” 当时左右为难,真想拒绝了事,但已到这地步,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就勉强答说“好吧!”他说,“你把眼睛闭起来,我说一句,你跟一句。”他说,“哦,主耶稣,”我跟着开始说,“哦,主耶稣。” 当我喊了一声主耶稣以后,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多久我不知道,后来祷告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眼睛睁开时,好象许多的愁苦、失落、压力、不安、都随着眼泪流走了。一股莫名的平安,笃定在我里面升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天晚上,我跟我先生说,“神好象是真的”。
第二天,我在简陋的院子里,抬头看天,发现天空怎么这么美丽蔚蓝,立刻觉得一切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我被一种光明感充满―是一种说不出来,但满有盼望与把握的感觉。然后我就打电话要求受浸,并且邀我先生一起受浸。我对他说,“如果你今天跟我一起受浸的话,我比我们俩结婚还高兴。”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我俩双双进入了神荣耀光明的国度。
我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想知道为什么。因此开始读圣经、操练祷告、过召会生活,我终于找到了人生之真谛实意,也找到了人生问题的答案。人是神造的器皿,专门用来盛装神的。但魔鬼撒但进来,使人有了原来不该有的罪,使我们做我们不愿意的事,拍马奉承、忌妒争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另一面,因为灵里缺少神装进来,若用知识、学问、名誉、地位来代替,里面怎么装也装不满,怎么搞也不对劲,没意思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只有当我们借着相信、呼求、祷告神,将祂自己放在我们里面作生命,我们就觉得什么都对,满足了。
回头看看,非常感谢我主耶稣,把我从千万人中分别出来。虽然因骄傲、自我,曾藐视、抵挡祂,连到得救前一刻,也没有诚意要祂,但因祂怜悯的心肠,眷顾我这个罪人的忧伤,把我的脚步引到了平安的路上。
这就是我认识神的经历。我原是一个在世上打滚的人,从地球东边转到西边,渴望寻求人生梦想,却屡次换来失望,是一个眼瞎、迷路的苦恼人。但如今,我的人生道路完全改了方向,从地上转到天上―在地过着如同在天,超越又充实的神人生活。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愿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祂!(孙金)
头上之天何蔚蓝,四周之地也青绿;
有一景色更鲜艳,无主之目从未睹:
鸟鸣变为更音乐,花美使我更快活,
自从我心能领略:我是属祂,祂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