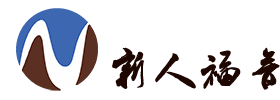一切出自神为着荣耀神
—访石油专家沈弟兄
你是否可以谈谈你的成长背景以及得救经历?
1937年我(Y. M. Shum)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父母就到了四川重庆,因此我从小就住在大姨妈家,由外公外婆照顾。外公外婆是基督徒,所以可以说我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但那时还谈不上有什么信仰。
读初中时我就离开家住进了学校宿舍。直至1958年,才到香港与家人团聚。到了香港后,我才知道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一遇到事情就说,“我们来祷告,求神怜悯。”祈求神的怜悯,是妈妈最常说的话。当时,虽然也有亲戚找我参加福音聚会,但我只是去勉强应付一下。
神的带领很奇妙。1961年9月,我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抵达学校的当天下午,我的导师亲自开车载我找房子住,结果四处碰壁。后来他想起有一位研究生是中国人,名字叫Daniel,因此就把Daniel从实验室找来帮助我。Daniel立刻表示没有问题。他是一位基督徒,和几位弟兄住在一起。所以我到柏克利的第一个晚上,就住进了当时的弟兄之家。当晚就有家聚会,隔天还有祷告聚会。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当他们在读圣经和祷告时,我并不觉得陌生。借着和他们相处,我感觉他们人都很好。虽然他们没有特别向我传福音,没过多久,我很自然地就受浸了,此后一直留在召会生活里。
你可以谈谈你的召会生活经历以及工作经历吗?
我因课余在餐馆打工,很快就买了一辆旧车子。每周五有家聚会,主日在旧金山有聚会,我经常去接送弟兄姊妹,就这样和我的太太认识了。我当时念机械系的热力系统,她念生物化学。她是58年到柏克利,63年取得博士学位。我们于64年结婚,婚后我就开始工作。到65年,她经由教授介绍去波士顿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的研究,我便到布朗大学念博士学位。我们在波士顿的家是打开的,聚会的人数不多,约五、六人,有时也在另一位弟兄家聚会。
68年9月我们搬到德州的休斯敦。那时在休斯敦只有两家弟兄姊妹,我们一家住在西边,James 一家在东边,他是一位西医的跌打医生。69年德州有移民行动,那时很多圣徒从德州各处搬到休斯敦,我们的家就成为他们暂时停留的地方。他们先落脚在我们家,然后可以去找工作,找房子。当时,有许多弟兄姊妹进进出出,在我们家也有聚会,后来弟兄姊妹才在市中心租下一个聚会的地方。
从1980年中国对外开放海上石油的勘探后,我就进入Texaco公司到中国发展。刚开始我主要是帮助公司去作些沟通的事,那时候,我一半的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印度尼西亚,负责计划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一个大油田的开发项目。1985年,我因工作的需要,全家搬到纽约。1992年,我被调到北京去负责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一直到1999年退休。2000至2007年,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同时还帮助深圳建立医学中心。
在中国作生意,可以说既容易又艰难,在乎有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中国的对外开放,无非是需要引进外国的技术、资金或外汇。我与中国官方打交道多年,对他们印象很好。和高层官员来往,我们彼此互信尊重,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一般公司例行的事情,都由办公室的经理出面处理。有必要时,我才出面。
那时,我跟中海油、中石油公司的领导多有往来。当然有特殊的情形才会见部长,跟领导们见面时通常是礼仪上的往来,多年来我们彼此双方有很好的合作,并且是很成功的。
在工作以及周遭环境的限制中,你是如何依靠主、联于主?
开始的时候,我帮忙带圣经去北京。因为我们以商务身份进关,不会被细查。每次我将带进去的圣经交给弟兄,然后由他去转发给别人。
1992年,我到国内长住,有时我们的家中有家聚会,因着环境的限制,人数也不太多,但与弟兄姊妹相聚,喜乐得很。虽然没有人因着聚集来找过我,但进来的访客都要经过登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弟兄姊妹的进出都是受监视的。我姊妹很有智慧,当她来北京时,就带一些糖果、巧克力送给小区的保安,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对他们说,沈太太经常会请人吃饭,请不要为难访客。
我们公司在国内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家有聚会。姊妹在北京的时候,她也会请人来家里聚聚,所以他们多少也会知道。
因着工作的需要,我每天出去是见不同的人,有时还要与国家领导级的人见面。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起头、如何结束。在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中方总是做主人,开会也好、讲话也好,都是他们开头,这对我是最好的。他们一开头,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哪个方向来,我就接着他们的话,从那里开始。当然我们见面,都有一个话题,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或是今天为什么见面,大主题是知道的,但如何开始不是完全知道。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个祷告,我的祷告很短:“哦,主啊,have mercy on me。”这个祷告是从我妈妈身上学来的,因为我妈妈一有什么事就是:“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无论我去开会、与人见面,永远都是这样很简单的一句祷告,神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带我过去。
在国内工作时你印象最深的事?
最令我紧张的就是1983年年底前要去见当时的总理。所有外国公司中,我们是第一个跟中国签海上石油合同的公司。那是一个盛大的世界性签约仪式,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公司合作。签约那天,几家商务公司包括Chevron、Texaco、AGIP的CEO都要去参加这个签字仪式。每个公司都预备了礼物,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出门的时候,我才想起忘了带那个礼物,这个很要紧,但我已上了车,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带礼物,到时会很尴尬。我心里想,这种事绝不可以发生,那时七上八下的心,真不是滋味。我只有不断地呼求主名,“哦,主耶稣。”这时想起,中方有安排一位叫小李的人帮忙处理相关礼节及住宿事宜。我于是问小李,“礼物带了吗?”当我听到他低声说:“带了,在后车厢。”我真是感谢主。只要我们一心为主,祂必会时时处处看顾我们。
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时,你是如何服事学生并传福音?
2000至2007这段时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我代表科大和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医院——深圳北大医院,使深圳的居民有病可以就地就医,不必到外地求医。除了医院之外,我们也建了一个医学中心。这项目由深圳市出资,北大医学部出人,香港科大协助研究。因此我跟深圳市的领导、北大的领导有多方面的接触。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我们作为领导的,要对新进人员说几句勉励的话。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刚才两位领导跟你们说的都很对,只是我们做人,不只对人对事都要对,我们对神更要对。”
在我们离开科大之前,深圳北大医院的院领导陪同我们去贵州,协助当地的医院开展,当时我姊妹也同行。一路上,我们和地方的领导、首长沟通交流。在一次的晚宴中,深圳北大医院心脏科的孙大夫提出一个关于神创造的问题。于是,我就趁机把圣经创世记和启示录简短地说了一下,当作福音传讲。
我打开在科大的办公室,是因为当时有这需要,就提供一点方便。感谢主,都是主的安排。我办公室所在的地点适中,很大,可能院长的办公室也没有那么大,里面放了一些桌椅,可供二十几人使用。我把办公室钥匙交给多位负责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在我的办公室学生可以晨兴并有祷告聚会。
我有时也帮学生们改改论文,写写介绍信。学生弟兄姊妹可以来我的办公室读圣经、交通。他们坐在那边,我在另一边办公,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时候打电话回中国还不是那么方便,若有从大陆来的交换生需要打电话回家,我就让他们随意使用办公室的电话。因为这不是公事的用途,账单来时,我就把学生们所使用的费用另外付给学校,学校的电话费很便宜,也没有多少钱。
有时,弟兄姊妹需要我帮忙替他们写信,写给领事馆或学校。遇到这类问题,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讲真话,不能讲假话。因为我是按着他们真实的情形来写信,写了之后,是由他们自己的名义发出去,我只是帮忙写,写的合情合理,但一定要真,不能造假。其中有好几件事情,本来看是很困难的,但感谢主,借着多方祷告最后都顺利地解决了。
我们的所能与所作,都是为着召会、为着弟兄姊妹。
可能跟家庭背景有关系。我从小跟着外祖父、外祖母,他们是做生意的。中国有一句话说:有土地就有财。我记得他们买房地产是整条街一间间的买,如果最后有一家不肯卖,他们就出高价买下。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对房地产一直都有兴趣。后来有点积蓄了,我就开始作房地产并考得执照。那时休斯敦教会准备买地建会所,我的执照正好派上用场;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想要移民,需要卖掉房子,才有现金可以立刻移民,因着我有这地产执照,就帮忙他们卖个好价格。在他们签合同时,我不拿佣金,让卖方的弟兄姊妹可以多拿些钱。会所的地产,我拿到的佣金也回馈他们,这样他们可以省下佣金费用。那时我们也曾贷款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有一句话我感触很深,就是我们实在是无有,但神是万有。这是很肯定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都是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我可能不是嘴巴,不善言词发表,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我们需要作一个尽功用的肢体,摆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让主来使用,配合主在地上的行动,愿主得着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