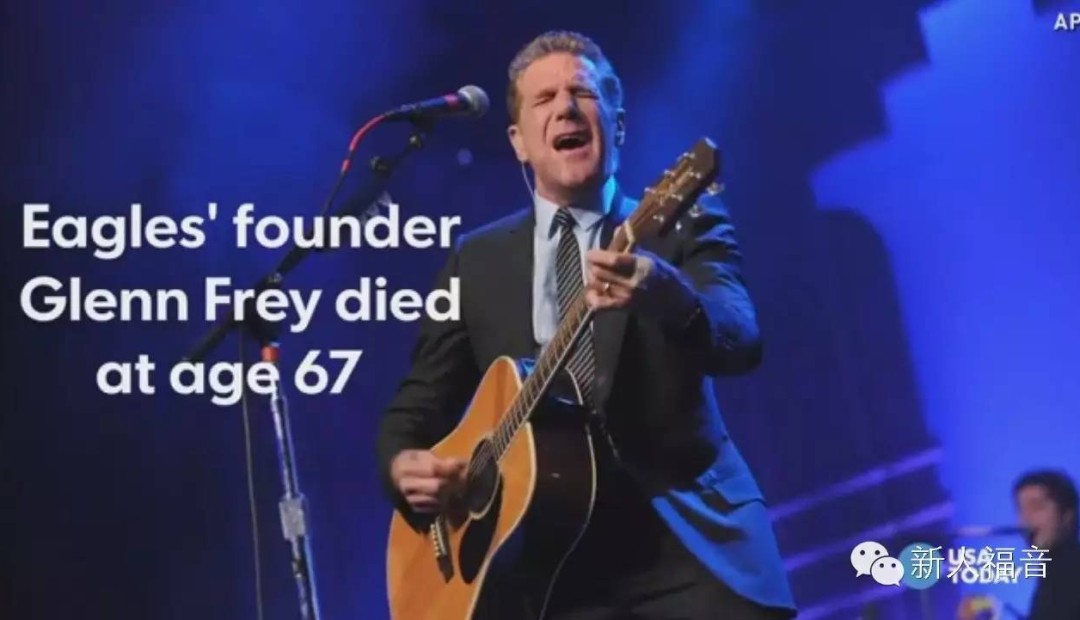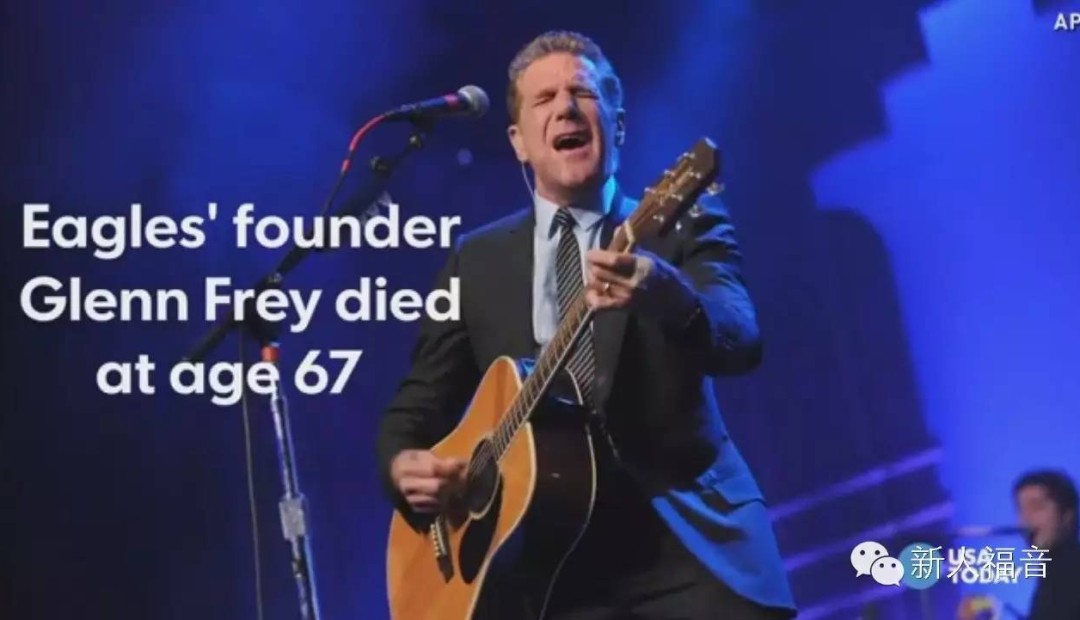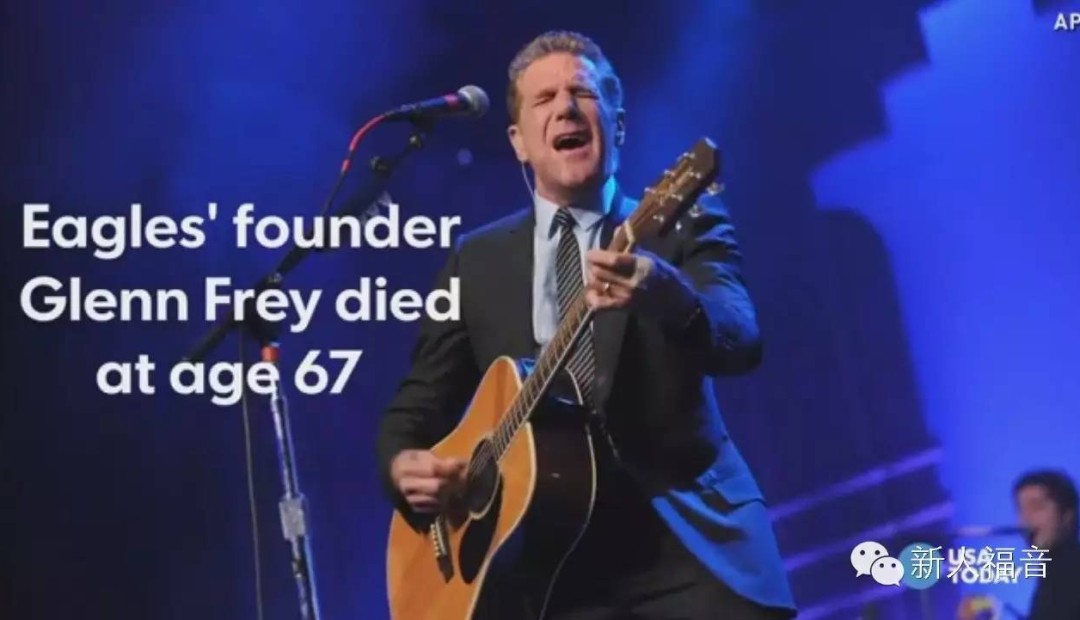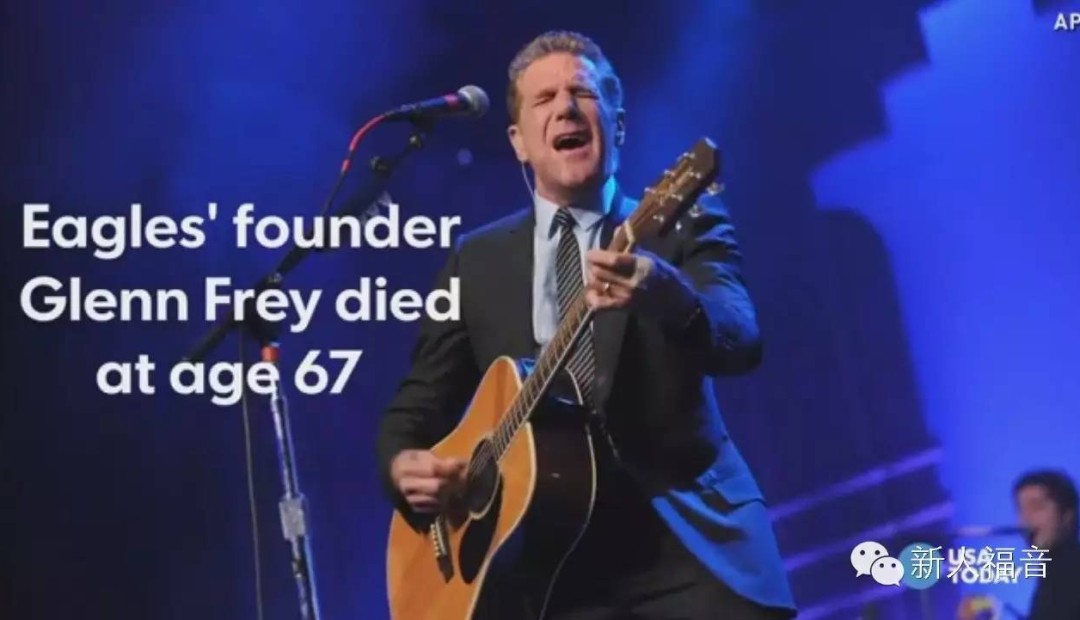
老鹰乐队的主唱去世了。格列·弗雷(Glenn Frey)于当地时间2016年1月18日在纽约去世。67岁。
第一次听到老鹰,是小学的时候。超长的过门,将近一分钟吉他层叠的渲染,把我带进了从未去过的加州。那时每周二我们还有队会课,在课堂上我们轮流宣誓要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下了课,在一部破旧的磁带机里,却幻想一座从未去过的酒店,一条从未见过的公路。
全世界的反叛,理想,青春和宣泄都倾倒在那些年间。年轻的我幻想着金斯堡时代的嬉皮,在加州沙漠里穿行,到了一个昏暗灯光的旅店。他们黑夜里暂时的居所,然而被豢养,被囚禁,被消磨,直到如今。
在旅店,歌者祈求说,“给我一点酒吧。”酒店的侍者却回答说,“自从1969年起,我们已经不再有(灵,精神抑或酒)。”
这真是一首充满了糟糕现实隐喻的歌,对自由的渴望催生出全世界反抗的风潮。68年巴黎的街堡,北京的风暴和伯克利汹涌的自由主义者,对着他们所在的正统社会祈求,给我们一点酒吧,一点生命,一点自由,一点爱。然而伴随着政治的铁幕,社会的冷漠,自由主义的崩溃,那一代人中的许多寻求者,被囚禁在“加州旅馆”这个人生的缩影里。如歌中所唱“你随时随地可以结账,但绝无法离开。”
这是一个全世界无神化的时代,人在自己的光里短暂欢腾,却不肯接受真光。东西方人在一个时间点,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反叛,最终同时落幕。人从不自由的困境出发,争取随心所欲的自由,最终发现这种所谓自由的巨大破坏,失去所有的幻想。老鹰乐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摇滚一样,盲目地追求着,宣泄着,重复着。他们成为至少两代青年的导师,领路者,却完全没有方向。
歌者和听众们也在摇滚鼓点的冲击下衰老,疲惫,最终死去。摇滚乐本来是对抗压抑、愤懑、不公而产生的,却因着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带进更大的压抑和愤懑。最终,我们会发现摇滚和它所反抗的世代一样,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正面的东西。
因着主的怜悯,十几年前我成为了基督徒。十几年前,一起玩摇滚的有一对情侣。有一年女贝斯手得了重病,男主唱不离不弃,表示爱她到永远。然后他等到了她醒来,等到她康复,等到她愿意嫁给他。然后他们离婚了。一切都无法避免地走向庸俗。那时候带着所有人真诚祝愿的誓言并没有成为真实,摇滚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爱的力量。当双方都累了,爱和生命就没有了。我也结婚了,妻子也成为基督徒,安宁度日,没有瞩目,没有宣誓, 日复一日,我们的爱愈发多,联接愈发紧密。
自从成为基督徒,我就很少去听摇滚了。每当我听见当日会冲击我魂的歌词,我大约会保持几秒钟的兴奋,然后就是困倦。当老态龙钟的教父唱《一无所有》,抛妻弃子的头条唱“我永远爱你”,那些所谓真诚的音乐完全脱离的真实。而现在我极其喜爱听那些少年时代被自己形容成白开水一样的舒缓的基督徒诗歌。里面或有高深的真理,或有温熏的爱,或有光明的盼望。这些歌在一个方面和摇滚一样是为了“与众不同”而作的,但在另一方面,却没有对人的仇恨、愤怒、没有肉体。因为一种爱的力量贯彻其中,使人失去了恨的可能。
那是在世界中,而不属世界的,一种完全超越世界的力量。
小时候哼着Dylon的You Belong to Me,觉得世界都是属于我的。可是你和我是属于谁的呢?摇滚既无法将世界给我,也无法使我属于谁。在四顾茫然,无法安息之时,幸好我们还能抬头看神。
如果您和我曾经一样,爱着,爱过摇滚,愿您认识更美不同之事。那些在摇滚里未曾见过,未曾听过甚至未曾想过的爱。耶稣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