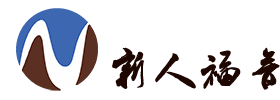儿时所在的大队叫南卡路,那里原来叫坷垃道,建国后改得文雅难懂了。
儿时所在的村是第六生产队,三排房子面南背北。北面的在山坡上,称上坎;中间的在山坡下,称下坎;南面的称为南坎。两条东西向的土路把三个坎隔开。我家在上坎的最西头,和下坎的国军家隔着路和几棵榆树。据说树那里建国前是个庙,叫太阳庙,村子也曾因此叫太阳庙。
国军姓祁,大我几个月,是我上学前唯一的朋友。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常去他家和他玩耍,那时的小孩子有衣服就不错了,天暖的时候有时就赤条条来去。
我偷藏了国军家的打火机,他妈妈找来时,就带她到秫秸帐子(篱笆)前,略略羞惭地从缝隙里拿出来。
一九七二年春,开学第二天,我们一起上学了。国军和我同桌,国军写的“席”占了方格本上下两格,我写的”毛”横总是多。
上学后我俩多了个朋友,住上坎东头的珠子。我们仨常在那几颗树下玩耍,其中的一件就是模仿《红色娘子军》,珠子装洪常青,我装吴清华,国军跑腿。有一次被同村大孩子们撞见,英雄珠子就遭戏弄了一番。
国军和我一起逃学了。逃学的兴奋过了,我正无聊在家,珠子带老师来家访,我就复学了。国军那时是独子,传说珠子带老师进他家门时,他正在吃妈妈的奶,于是害羞地跳窗逃了。国军没有返校,留了一级。我的小学毕业照里没有他。
珠子搬去了黑龙江,国军家也搬到南坎,找他的机会就少了些许。一九八〇年,我去三十里外的岔路口读高中,刚好国军也转学去那里读初中,住在亲戚家。我就常去找他。
我们常常周六下午一起走回家,周一凌晨一起走回学校。从家到学校要走三个小时。不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走了多少个来回,看了多少风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这样记着:
“早晨三点十分就起来了。自己收拾一点吃的,叫国军,适好他来叫我,同去学校。到了三家子东面,天阴了。北方有一条长长的黑云带,向这方滚来,后面的雨也奔来了。速行,欲躲雨。一会儿,那云断为几截。而自东方沿天边上,有一条晕黄的似光的长带,不知是何物。又一会,断带复接成线,雨也到了,阴森的很。忽然地下一亮,未明白怎么回事,霹雳声已到了,很吓人。我俩吓得急弯腰。一会儿,去烧油的地方去避雨。雨还很大,此时头晕、困倦,差一点睡着了,只好同国军回家了。”
翻看日记,哑然失笑,少年记日记居然也是春秋笔法!羞于记下被雷哭了,反倒描述起风云来。那条路正在兴建,附近没有人家,只有一个烧油(就是加热沥青)的工地。那是至今离我最近的雷电!雷落下时,我俩惊恐地抱在一起,蹲下大哭,上学的心也被雷没了。雨停了,我们就一起悲切回家了。第二天缓过精神,重新走去学校。
我去了南方上学,国军留在乡下。每次回家,还去找他。国军的奶奶是我远房的舅奶,老人家常夸我的手又小又软。其实我那时可能缺钙,国军却一直很白、很秀气。
父母搬进县城,回故乡的机会越加少。一九九一年春节回南卡路,国军搬回下坎,已经结婚生子。我为他儿子照了张照片,却忘了给他照。我也从来没有他的照片。二〇〇一年夏回南卡路,他搬到上坎的西面,我们在一片杨树林里遇见,只来得及握手寒暄。那时国军胖了许多。
二〇一〇年夏,又一次回到南卡路,那时我已经是基督徒。国军的奶奶、父亲已经去世。没找到国军,只找到国军的妈妈和妻子,给她们传福音时,留下一张福音单张。
两年后,老家传来消息,二〇一二年深秋,国军收好了庄稼,装修好了城里的新房子,喝了两杯啤酒,就脑出血去世了。
二〇一三年我再次回南卡路,又见到国军的妈妈、妻子,在眼泪中再给她们传耶稣的福音时,我的朋友却已经永远不在了。
那次终于见到国军的照片,却是十几年前的,还是那么白、那么年轻。没等变老,他就不在了。
得救后从来没能见到国军,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告诉他,耶稣是神,可以赐他永远的生命。
那张福音单张有没有传到国军手里?国军究竟有没有接受过福音呢?